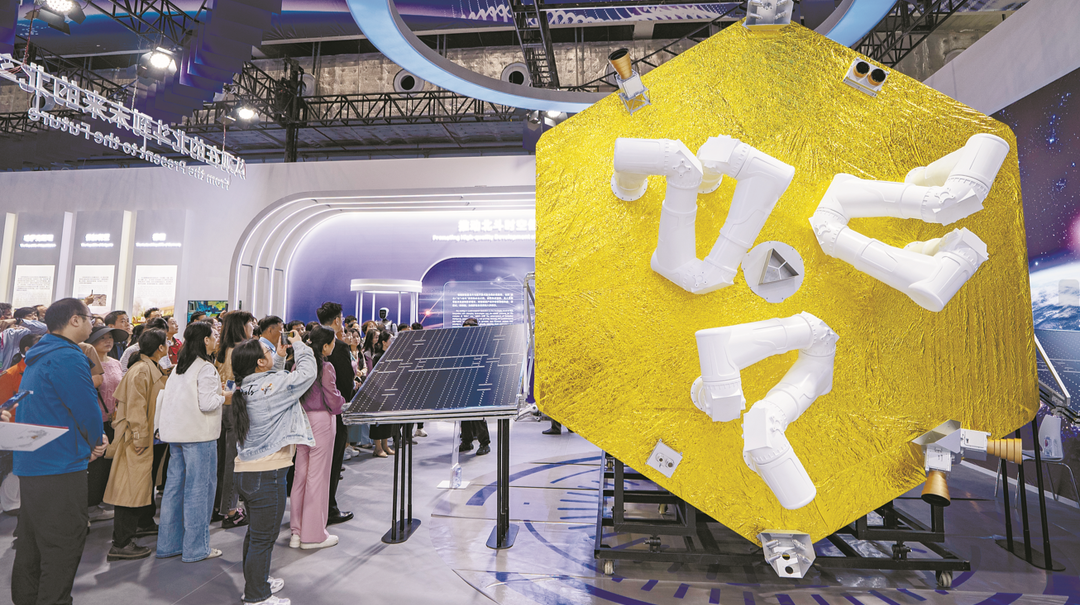覃秀珍。通訊員 攝
【名片】
覃秀珍,女,苗族,1979年7月出生,中共黨員,基層中小學正高級教師。1998年7月參加工作,現任教于洪江市第六中學。她扎根鄉村教育27年,耐心引領山區孩子健康成長。曾獲湖南省優秀教師、懷化市教學名師、懷化市師德楷模等榮譽稱號。
【日志】
9月17日,星期三,晴。
新學期開學已有半月。站在講臺上,望著底下幾十雙眼睛——有的明亮專注,有的還有些漫不經心,我知道,這段時間,比傳授知識更重要的,是幫他們把“心”收回來,把“習慣”立起來。
這些剛邁入初中的孩子,正站在人生新階段的起點上。“同學們,初中意味著什么?”我告訴他們,“意味著你們要有理想、有擔當,要對自己有要求。”為了幫助他們在新的階段明確方向、樹立目標,我讓每個人在周記本上寫下一句激勵自己的話,作為這一學期的座右銘。
我從坐姿、筆記、晨讀、閱讀到寫周記,一點一滴耐心引導。這些習慣,看似簡單,但對很多留守家庭的孩子來說,卻需要反復提醒。
能有這份耐心,源于我自己也曾是個差點“掉隊”的孩子。小時候家里窮,初中時我輟學打工。我以為這輩子就只能這樣了,直到老師踩著泥濘的山路,一次次找到我家,一遍遍勸我回課堂。從那時起,我就在心里種下一顆種子:要像我的老師那樣,用愛去守護更多孩子。
師范學校畢業后,我主動選擇回到鄉村,第一站是深渡苗族鄉的上坪村小。剛走上講臺那天,我心里頭泛起一陣落差——全班總共就12個孩子,空蕩蕩的。要知道,之前我在城區學校實習時,每個班都有四五十個學生,熱鬧得很。
可當我低頭瞧見孩子們腳上的鞋時,心里那點失落又悄悄消散了。他們大多穿著沾著泥點的雨靴,褲腳還卷著,一看就是早上踩著山路來的。可他們的眼睛卻亮亮的,直勾勾盯著黑板,那股子想學好的勁兒藏都藏不住。
那時學校條件是真艱苦,土墻漏風,地面是夯實的泥巴,一到冬天上課,下半身凍得幾乎失去知覺。但我從不后悔。因為我深知,越是這樣有質樸渴望的孩子,越需要有人幫他們走出去。
后來我調到洪江市六中,這里留守學生也多,學習基礎也弱,但我從沒放棄任何一個孩子。我始終相信,只要用愛澆灌,孩子們終會成長。
記得去年接手的一個初三班,有個叫楊俊的男孩子,兩年沒說過一句話,不交作業、不回答問題,教他數學的老師跟我說,兩年來從沒聽見他應答過一聲。我當時就想:這學期,我一定要讓他開口。
我制造機會讓他來辦公室幫忙,跟他聊天,他不說話我就讓他寫字代替,發現他的閃光點,在班上公開表揚他。經過20多天的努力,他終于開口了。那一刻,我眼淚差點掉下來,我仿佛聽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。
他后來告訴我,是因為非常自卑,才把自己封閉起來。畢業時,他主動來找我聊天,還拍了合照。他說:“老師,是您讓我有了自信,有了面對大家的勇氣。”
這樣的孩子,我遇到不止一個。丁熙誠剛上初中時,語文成績常年在30多分,字寫得更是潦草。可我發現他上課總愛舉手,眼神里藏著對知識的渴望。我沒批評過他一句,反而每次練字都站在他旁邊,手把手教他握筆,跟他說“你上課這么積極,說明你很聰明,只要把字練好、認真完成作業,語文肯定能及格。”
他每次有進步,我都會在班上表揚,還給他評了進步獎。慢慢地,他欠作業的次數少了,字也越來越工整。初三模考時,他居然及格了,全班都為他鼓掌。更重要的是,他找到了學習的信心,端正了人生的態度。
這些孩子的轉變讓我認為自己的堅守是值得的,還有他們畢業時寫下的留言,我都小心地收在抽屜里,每次翻看,都覺得渾身是勁。
“你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?”總有人這樣問我。曾經,好幾所城區學校的校長都向我拋過橄欖枝,希望我調到他們學校去,說他們的學生更好教,更容易出成績,我都委婉拒絕了。
對我來說,無論在哪里教書,都是幸福的。教育是一場漫長的守望,我愿一直守在這鄉村校園里,等每一個孩子都能走出屬于自己的路。畢竟,我也曾是被光照亮過的人,現在,我想做那個舉燈的人。
(湖南日報全媒體記者 劉鎮東 整理)
責編:伍鏌
一審:伍鏌
二審:印奕帆
三審:譚登
來源:華聲在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