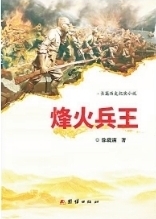
陳善君
作為岳陽新墻河的子弟,為紀(jì)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,作家徐載滿滿懷感情與責(zé)任,歷時(shí)兩年多,輾轉(zhuǎn)奔波于湖南岳陽、常德、衡陽,陜西漢中及湖北武漢等地,收集整理抗日戰(zhàn)爭時(shí)期與湘北會(huì)戰(zhàn)相關(guān)史料,數(shù)易其稿,創(chuàng)作出版長篇?dú)v史紀(jì)實(shí)小說《烽火兵王》(團(tuán)結(jié)出版社出版)。
以“大歷史觀”燭照,還原“湘北大捷”
新墻河無聲無息日夜流淌,映照、見證和記載了湘北兒女與抗日戰(zhàn)士曾在此并肩戰(zhàn)斗的可歌可泣的光榮史詩。
《烽火兵王》28萬字,圍繞第一次長沙會(huì)戰(zhàn)“湘北大捷”真實(shí)歷史事件展開。作品通過對(duì)“兵王”曹錫及其戰(zhàn)友甘永小、焦曉天等為代表的一批國共抗日軍民濃墨重彩的描寫,生動(dòng)講述了新墻河兩岸抗日軍民浴血奮戰(zhàn)的英雄事跡,為抗日英雄立傳、為岳陽人民的母親河之一——新墻河銘史。
小說把新墻河大捷放在中日22次大會(huì)戰(zhàn)的整體視域下來觀照,放進(jìn)第一次長沙會(huì)戰(zhàn)的整體部署中來反映,拉伸了小說歷史敘述的長度;小說不僅描繪國民革命軍的正面戰(zhàn)場抗擊,也反映了中共湘鄂贛及岳陽地下黨發(fā)揮的重要作用,延展了小說歷史敘述的寬度;小說把中日戰(zhàn)爭包括這場戰(zhàn)斗的矛頭,對(duì)準(zhǔn)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殘暴與中國人民愛好和平反抗壓迫的較量上,這就具備了小說歷史敘述的深度;小說不僅從中國人民、中國媒體的視角來寫戰(zhàn)爭,還從日本各方、外國各界的視角來寫戰(zhàn)爭,這就拓展了小說歷史敘述的維度。作者在寫作中的“大歷史觀”,使得這場戰(zhàn)爭的真實(shí)度和慘烈度在書中得以更加充分地呈現(xiàn)。
以“大文學(xué)觀”契入,縫合事實(shí)與虛構(gòu)
《烽火兵王》的紀(jì)實(shí)性明顯強(qiáng)于文學(xué)性,因其歷史事實(shí)本身就具備傳奇性、故事性,吸引力和感染力。然而畢竟是小說創(chuàng)作,“戰(zhàn)爭”的勝負(fù)結(jié)果是已知的,而其過程是“已逝”的。只有適當(dāng)虛構(gòu),才能完成小說的“起承轉(zhuǎn)合”,讓人物“站立”起來。
小說中的人物在現(xiàn)實(shí)中是有原型的,從主人公曹錫開始。曹錫是確有其人其名的,他在“湘北會(huì)戰(zhàn)”中,當(dāng)戰(zhàn)友們都倒下后,仍頑強(qiáng)地堅(jiān)守陣地,殺敵數(shù)百。他的事跡還登過報(bào),書中說到被政府獎(jiǎng)勵(lì)了30塊銀元,也是真有其事,其被稱為“兵王”也不假。如今新墻河抗戰(zhàn)史實(shí)陳列館里,還有曹錫的事跡介紹。
作者在小說的扉頁列了《人物小傳》,統(tǒng)計(jì)了涉及到的抗戰(zhàn)軍民,計(jì)有33人。這些人物包括漢奸大都是真有其人的。究其分量來看,《烽火兵王》的虛構(gòu)占到一半,然論其重要性,則不足十分之一矣。一虛一實(shí)間,“兵王”就活在人們的眼前和腦海了。
以“大創(chuàng)作觀”統(tǒng)攝,形成“超文本”表達(dá)
單論文學(xué)性,《烽火兵王》并不見長,倘論“文本”性,其綜合價(jià)值則高。《烽火兵王》熔史記、傳記、游記、雜記于一爐。其為新墻河“大捷”存史、為“兵王”立傳,也為湖南岳陽和陜西漢中推薦旅游資源。
小說通過追敘曹錫上山砍柴、求學(xué)遠(yuǎn)足、任職立業(yè)等成長歷程,巧妙地將“石門棧道”、武侯祠等勝景寫進(jìn)書中。之于岳陽,作者更是手到拿來、游刃有余,八百里洞庭、荊楚大地、岳陽樓、岳陽火車站、新墻河、鐵路大橋、新墻老街、大云山、張谷英村、麻布大山等等這些帶有標(biāo)志性的古今建筑,一一成為小說中眾多人物活動(dòng)的舞臺(tái)。
至于雜記,作者的用意則更為深長。凡有所及史料、風(fēng)俗、文物、遺址……作者都不厭其煩悉數(shù)娓娓道來,這也是作者在為一部關(guān)于新墻河大捷的影視作品腳本做準(zhǔn)備。
以“大時(shí)代觀”匯入,鏈接“傳奇敘事”
《烽火兵王》無疑是謳歌英雄、謳歌全民族軍民抗戰(zhàn)的宏大敘事文本,然而作品卻從人性的角度挖掘主人公曹錫“怎么由一個(gè)農(nóng)家子弟、普通士兵,克服了對(duì)戰(zhàn)爭的恐懼,怎么提高射擊本領(lǐng),如何在艱苦的環(huán)境下,甚至在敵人施放毒氣的情況下,堅(jiān)固掩體,保護(hù)戰(zhàn)友與自己的故事。”作者并沒有故意拔高、神化他們,而是貼著人性寫了他們的內(nèi)心世界,以細(xì)節(jié)和心理的真實(shí),寫出了這些人物的成長經(jīng)歷和偉岸精神。
特別要提及的是,這本“兵王”傳奇敘事還帶有強(qiáng)烈的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色彩和氣息,在結(jié)構(gòu)上可能不是那么嚴(yán)絲合縫,然而整篇敘述卻讓人讀著“過癮”,比較適配年輕人的閱讀訴求。從“超文本”到“超鏈接”,《烽火兵王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成為傳統(tǒng)“傳奇”創(chuàng)新敘事路徑的一種探索。
(作者系湖南省文藝評(píng)論家協(xié)會(huì)主席、秘書長)
責(zé)編:潘華
一審:潘華
二審:印奕帆
三審:譚登
來源:華聲在線








